
關于「水平線設計」
「水平線設計」是中國當代設計的代表之一,擁有多名優秀年輕設計師的國際化團隊。自2003年成立至今,水平線設計始終秉承創新精神,在建筑設計、室內設計、景觀設計、產品設計等領域開拓深耕,竭力為業主提出設計與工程方面的最佳解決方案。
修復、保留,從內部生長而出……如果是總結,章堰文化館便可以就此總結了。我很喜歡“生長”這個詞語,過去未來及現在都可以被囊括在其中,包含著除開“生命”本身的等等引申義。

石拱橋、城隍廟、灰瓦白墻——這是個傳統到一定層面并且本身就擁有完整意境的外環境,似乎很應該按照常規的手法,從對象符合觀念的方式去理解和構建新的存在。但同時也可以換個角度,回到先天結構,回到人與天地本身,借助外界所獲得的感覺經驗、直覺、印象等等,將人面對這片土地時的種種情感現象融合,從主體建立起客體,由客體承載起主體。
玻璃、殘磚、白色混凝土坡屋頂——我一向喜歡“關系”一詞。不單一固定,多種組合關系,拼接、比對、承前顧后,而渾然是一個整體。用兩年半的時間,在有限的空間內造出好似無盡的園,游走的動線得豐富,心理預期得調足,水不止是水,墻也不止是墻,與樹、與鳥、與香味,排列組合成數列的冪次方。我一直覺得空間不僅僅是空間,還是五感的集合點,需要有著耐品的對比和張力,身在其中才能產生完整且多重感。
章堰文化館的意義是以“時間”為前提的。歷史、當下與未來之間的并置探討,并不只是對廢墟與新生的考量,而是一種重疊與重構,是在時間軸線上討論一種非單一線型敘事手法的可能性。當新的變舊,舊的消融進時光,更新的又再會出現后,此時的新舊又是怎樣的一種姿態,進入怎樣一種日常?
兩棵古樹依然在原地高聳著,隨著天光變幻,年復一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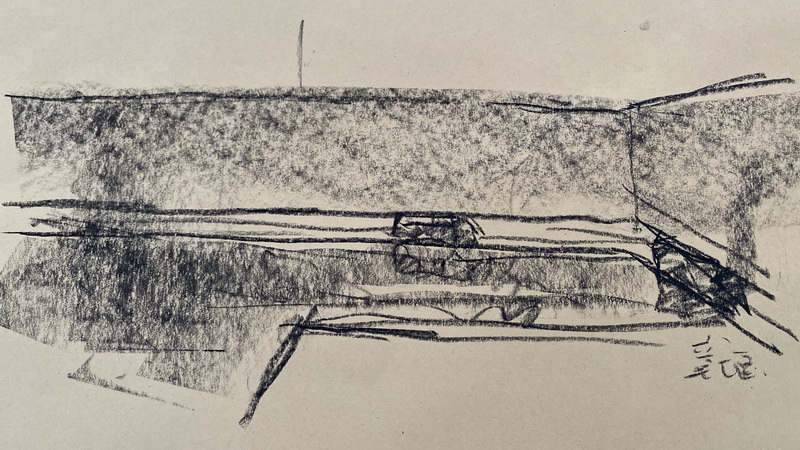
琚賓手繪


章堰村位于上海西郊的重固鎮,是上海古文化發源地,福泉山文化的代表之一。這座擁有千年故事的古村落從唐宋年代起臨水而筑,那時的章堰十分繁華,章楶,蘇軾,任仁發,米芾等賢士皆在詩文中提及或到過此處。

經過歷史變遷,章堰村空心化嚴重,現已不復以往的繁華,村里現存有清代、民國建筑和建國后洋房。在新型城鎮化的政策背景下,章堰村迎來改建與復興。

生存,生長,新生,是我們對章堰村以及中國現狀下同類村落的改造和復興策略,不是推倒重建,不是修舊如舊,而是遵循歷史的發展脈絡,將當下的發展觀念和功能需求置入其中,重新梳理和組織布局、功能業態、新老關系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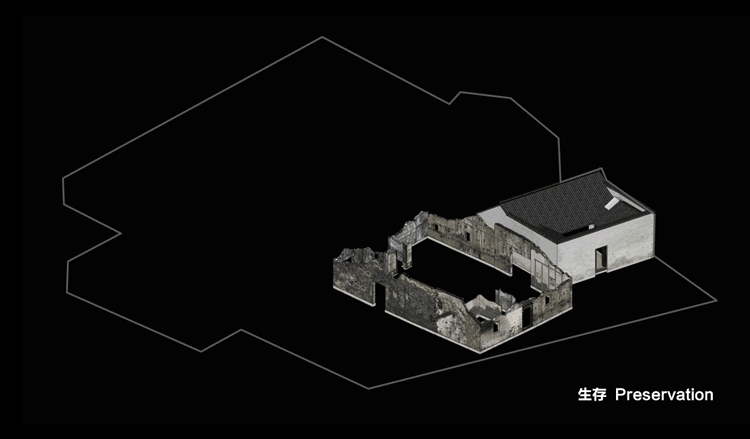
「生存」
“老建筑”是章堰村的歷史,文化的沉淀,我們通過加固、修繕等方法,讓老建筑以更好的狀態「生存」下去。
「生長」
破敗、無法再使用其內部空間的老建筑,我們需“清理”破敗及無法使用的部分后,從中「生長」出與原老建筑有關聯的新建筑,使“新老”建筑共存。
「新生」
新建筑是新時代與新功能的呈現。為滿足新的使用需求,我們也會從空地中「新生」出一些當代建筑。

文化館基地很有代表性。其中包含了原村史館(清朝老房子)、章家宅(破敗的晚清老房子)、及一部分空地。相鄰的房屋有80年代二三層洋房和宗教建筑——城隍廟。
根據基地條件,文化館設計由三個不同特點的展示空間以及水院組成。





章家宅殘破比較嚴重,但外墻風貌較好且完整,我們對外墻進行了加固和保護,在保護好的外墻內新建了展廳一。展廳一沿用了章家宅“四水歸堂”的建筑制式,并與老墻脫開最少處三十公分距離,是我們對歷史的尊重與致敬;展廳一內部有窗戶,建立起與章家宅外墻的聯系。

村史館保留較好,我們對內部木承重結構做了加固和修繕處理,作為展廳二。地面返潮嚴重,我們重做了地面防潮,改造了地面材料為陽極氧化鋁板,與展廳一地面一致,空間產生延續,且讓空間看起來更明亮和寬敞。老的墻面,屋面,內院保留下來。



通過復原研究,村史館北側空地原為村史館的二進院,現有基礎遺存,我們在原有基礎位置上新建展廳三,展廳三墻面、地面及天花板皆為陽極氧化鋁材料。均質的金屬材料帶來某種“未來”感的體驗,與展廳一的“當代”、展廳二的“傳統”構成一段動態的體驗。

出展廳三便是基地北側的空地。我們在保留空地上的大樹及竹林的基礎上新建了休息區和水院,供人們休息和討論。新建的建筑皆采用白色清水混凝土材質。白色清水混凝土材質呼應了當地建筑外墻紙筋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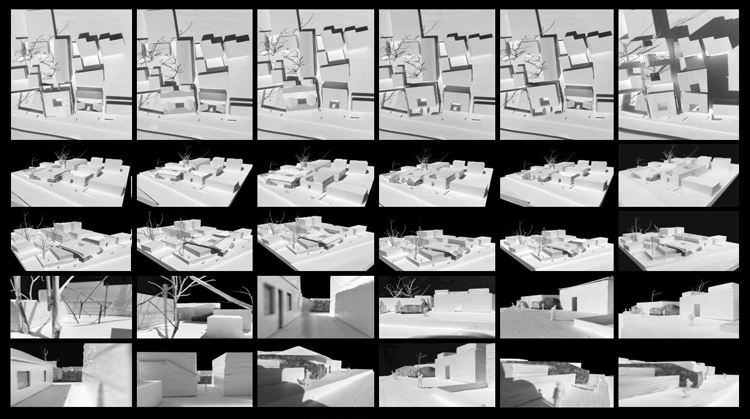

關于「水平線設計」
在設計中,「水平線設計」善于發掘傳統文化中的更多可能性,賦予每個設計以鮮明的個性和旺盛的生命力。水平線設計通過對東方傳統文化、藝術與哲學等方面的提取和運用,配合數字化分析工具和國際先鋒的設計方法,致力于創造真正屬于中國的現代巔峰設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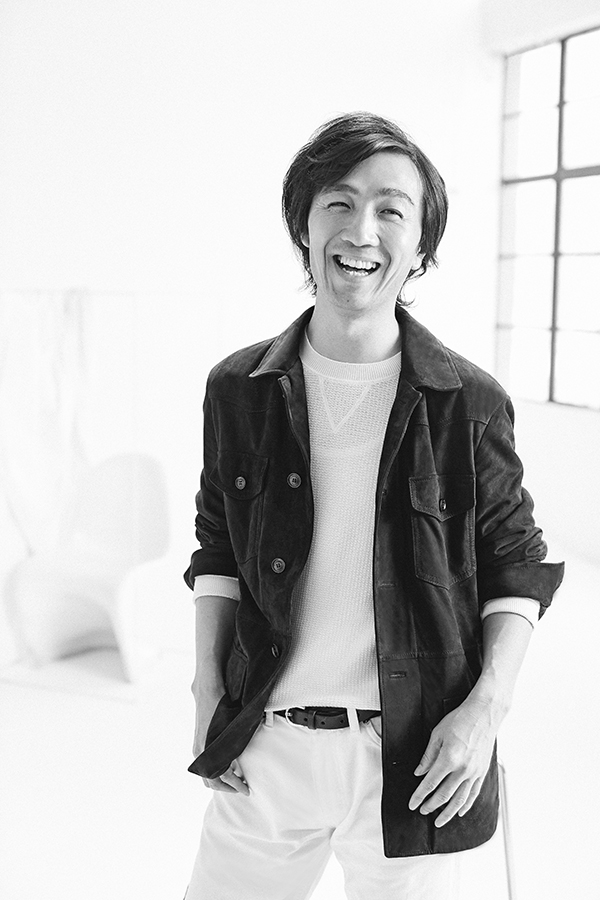
設計師、創基金理事
水平線設計品牌創始人兼首席創意總監
